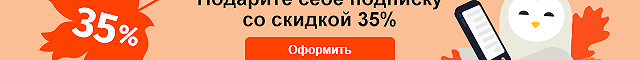
第四章
默克跑過樹林,踉踉蹌蹌的奔下泥坡,在樹木間穿插前行。他全速奔跑,白木森林的樹葉在他腳下沙沙作響。他眼看前方,雙目不離遠處升起的陣陣濃煙。濃煙遮蓋了血紅的日落,他心裏更是著急。他知道那女孩就在那邊某處,也許此刻正被殘殺,但他無法再跑快些。
殺戮與他很有緣,似乎每天都找上他,就像其他人被喚回家吃晚飯一樣稀鬆平常。他和死神有約,他媽媽以前常說。這句話在他腦海中縈繞不散,困擾他大半生。她說的話難道應驗了嗎?還是他出生以來就有一顆黑星高掛在他頭上?
對默克來說,殺人是家常便飯的事,就像呼吸和吃飯一樣︰為何殺、如何殺,一概不重要。他越是細想,越是感到極噁心,彷彿想把他整個人生嘔吐乾淨。縱使他的身心都向他尖叫著要他轉身而去,開展新生活,繼續往厄爾之塔朝聖,但他實在辦不到。暴力再次召喚他,現在可不能坐視不理。
默克越來越接近滾滾濃煙,煙味撲鼻,開始呼吸困難,然後一種熟悉的感覺襲來。那不是恐懼,他早已習以為常,甚至不是興奮,而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是他快要化身殺人機器的預感。每次他上戰場便有這種感覺-那是他自己的戰鬥。在他的戰爭中,他總是面對面殺掉對手,不必像那些花巧騎士般戴著面罩或盔甲,享受人群的掌聲才出擊。在他看來,他的戰鬥最講求勇氣,是為像他那樣真正的戰士而設的。
然而默克奔跑的時候,感覺到這次有些不一樣。通常默克並不理會誰生誰死,那不過是工作。那樣他便能保持頭腦清楚,不會被情緒蒙蔽,但這次大不相同。這麼多年來,他第一次不是受聘行動,而是出於自願,純粹因為他可憐那女孩,希望撥亂反正。他投放了私人情感,而他不喜歡這樣。他後悔沒有及早行動,反而把那女孩打發走。
默克穩步跑著,身上沒有帶任何武器,也不需要。他的匕首掛在皮帶上也就夠了。說實在,他未必需要用上它。他選擇不帶兵器上戰場,可以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況且,他大可以奪走敵人的兵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不管走到哪裏,隨時都有兵器可用。
默克衝出白木森林,叢林的景色都換成開闊平原和起伏不定的山丘,巨大的紅日正除除落下。山谷在他眼前延伸,黑雲蓋頂,濃煙密布,彷彿上天動怒了似的。只見那裏洪洪烈火,定是那女孩的農莊給燒毀了。默克能在這裏聽到那些惡徒的歡呼聲,聽得出他們嗜血如狂,心情大好。他熟練的仔細觀察罪案現場,立即發現了十二個人,手上的火把照亮了他們的臉。他們跑來跑去,把一切都燒光。有些人從馬廄跑到房子,在草屋頂點火;其他人則用斧頭殘殺無辜的牛群。默克看見他們其中一人扯著一個人的頭髮在泥地上拖著走。
一個女人。
默克懷疑正是那女孩,不禁心跳加速-不知她是生是死。那男人把那女人拖到她家人面前,全都用繩子拴在牛欄上。那是她的父母,旁邊看來是她的幾個妹妹。一陣微風吹過一團煙雲,默克瞥見那女人滿頭泥濘的長金髮,他便知道正是那女孩。
默克感到一陣激動,衝下山坡,落在泥濘地,在濃煙烈火之間奔跑,終於看清發生了甚麼事︰那女孩的家人靠在牆上,咽喉被割斷,早已死去,屍首軟趴趴的被掛在牆上。默克看到被拖走的女孩仍然活著,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們要把那女孩拖到她家人面前,她極力掙扎著。他看到一個惡徒拿著匕首等著她,便知道她便是下一個受害者。他來得太遲,救不到她的家人,但還來得及救她。
默克知道自己必須乘其不備出手。他放慢腳步,冷靜的大步走到泥濘地的中心,彷彿時間充裕,等待他們留意他,希望迷惑他們。
很快,他們其中一人發現了他。那惡徒立即轉身,看到一個男人走過血腥現場卻不為所動,吃了一驚。他向他的同黨大叫。
默克漫不經心的走向那女孩,感覺到許多困惑的眼神落在他身上。那拖拉著女孩的惡徒回過頭來,看到默克便停下來,放開了手,任由她跌落在泥地上。他轉身和其他人一起包圍默克,準備戰鬥。
「這是甚麼人?」看似是他們頭目的男人叫道,正是拖拉女孩的人。他定睛瞪著默克,從皮帶中抽出劍來。其他人圍著默克,越走越近。
默克只是凝視著那女孩,確認她是否活著、有沒有受傷。看到她在泥中扭動,慢慢鎮靜下來,抬起頭,回眸看著他,一臉茫然。默克知道自己還來得及救她,放下心來。也許這是踏出那救贖長路的第一步,他發現也許一切不是從那座塔萌發,而是在這裏開始。
那女孩在泥濘中翻身,用手肘撐著起來。他倆四目交投,他看到她眼中滿是希望。
「殺了他們!」她尖聲叫道。
默克保持冷靜,繼續漫步走向她,對圍著他的人視若無睹。
「原來你認識這女孩?」那頭目向他叫道。
「她叔叔?」其中一人嘲弄道。
「失散了的哥哥?」另一人笑道。
「老鬼,你來保護她嗎?」另一人譏道。
其他人大笑起來,越逼越近。
默克不露聲色的估量所有敵人,以眼角打量著他們,估算著他們的人數、體格和速度,還有手上的兵器。他剖析著他們肌肉和體脂肪的比例、他們穿的裝備、行動快慢、穿著那些皮靴轉身時有多快。他留意到他們手上的兵器-粗製小刀、破舊匕首、鈍劍-分析他們手握兵器的方法,放在一邊還是握在面前,用的是哪一隻手。
他發現大部分都是外行人,沒有人真的在意他。除了一個人。手執弩弓的那個人。默克在心中暗忖要先把他除掉。
此刻默克進入不同的領域、不一樣的思維方式,判若兩人。在戰鬥中,這個他總會自然出現。他沉沒在自己的世界中,失去控制,完全放棄自我。那個世界的他告訴他能以多快的速度有效的殺多少人,以最小的力量造成最大的傷害。
他為這些人感到難過,他們對自己的處境一無所知。
「喂,我跟你說話呢!」他們的頭目叫道,離他不夠十尺,拿著劍冷冷一笑,快步上前。
但默克仍然繼續走他的路,看來冷靜而且面無表情。他非常專注,腦中已完全聽不到他們頭目說的話。他不會跑,也不會流露敵意,要等時機成熟。他感覺到那些人對他毫無動靜摸不著頭腦。
「喂,你知道自己快死了嗎?」那頭目繼續說。「你聽到嗎?」
默克繼續自顧自的走著,激怒他們的頭目。那頭目終於沉不住氣,怒吼一聲,舉起劍衝前,向著默克的肩膊一揮。
默克也不著急,仍然沒有反應。他漫步走向敵人,等到最後一秒,提醒自己不要繃緊身子,也別作任何反抗。
他不動聲色的等著,早就知道敵人把劍舉到最高點的時候,就是露出弱點的瞬間。然後默克以迅雷之勢一個箭步向前,像頭蛇似的用兩隻手指擊向那男人腋下的施壓點。
他的敵人驚訝的鼓起雙眼,神情痛苦,手中佩劍隨即脫手。
默克踏近一步,一手環扣著那人的手臂,緊緊鎖穩;同時他抓緊那人的後腦,控制他的身體,作盾牌之用。因為默克擔心的不是這個頭目,而是在他身後拿著弩弓的敵人。為了拿到人肉盾牌,默克才選擇先攻擊這笨蛋。
默克轉身面對弩弓手。如他所料,弩弓手早已蓄勢待發。默克隨即聽到弩弓射出弓箭的咔嚓聲,看著弓箭劃破空氣向他飛來。默克緊抓著他面容扭曲的人肉盾牌。
然後默克聽得一聲喘息,那人肉盾牌在他手中震動了一下,痛苦得大叫,而默克也突然感到一陣痛楚,就像給刀子插中腹部一樣。一開始他感到奇怪,然後發現弓箭射穿了人肉盾牌,箭頭剛好刺到默克的肚子,只刺入半寸,不足以令他受重傷,但已夠他好受了。
默克計算著上弓的時間,隨即丟下那頭目無力的身驅,搶過他手中的劍擲了出去,向那手執弩弓的惡徒直飛過去,插入他的胸口。他慘叫一聲,雙目睜圓,驚詫不已。他放開弩弓,倒在旁邊。
默克轉身看著其他惡徒,全都一臉驚慌。他們最強的兩人居然都死了,頓時不知所措。他們面面相覷,一聲不響。
「你是誰?」終於,他們其中一人緊張的叫問道。
默克露出笑顏,掰著手指節,準備享受一場打鬥。
「我嘛,」他答道。「是你們的惡夢。」
第五章
鄧肯與他的軍隊騎著馬,幾百匹馬的馬蹄聲如雷貫耳。他帶領軍隊離開亞爾戈城,徹夜向南行。他最信任的指揮官與他並肩而行,安溫和艾瑟菲爾分別在兩邊,只有維達留守佛理斯。還有幾百人在他們身邊列隊而行,一起上路。與其他統帥不一樣,鄧肯喜歡與士兵們並肩而行,從不把這些人當成手下,而是戰友。
他們整夜前行,寒風吹過他們的頭髮,腳下踏著白雪;鄧肯很高興能動身前往打仗,再也不用大半生躲在佛理斯城牆後苟且偷生。鄧肯回頭一瞥,發現兩個兒子布蘭登和布拉克斯頓和他的弟兄們一起前進。他為兩個兒子能夠同行而自豪,他並不像對女兒那樣擔心他們。時間逐點過去,雖然鄧肯一再告訴自己不用擔憂,但他夜裏想起的始終是凱娜。
他琢磨現在她身處何方。他想到女兒獨自越過艾斯卡隆,身邊只有蒂德蕾、安鐸和李奧,整顆心便抽著痛。他知道這趟旅程對許多老練的戰士來說也是險阻重重。假如她能倖存,便能以偉大戰士的身份回歸,甚至比和他同行的任何戰士都要強大;要是她死了的話,他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但情況緊急,他只能孤注一擲。現在他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她通過試煉。
他們跨過一座又一座的山丘,風勢越來越大,鄧肯看著連綿不盡的平原,在月光下展延開來,他想起他們的目的地:艾希佛斯。那城市是海上要塞,建於海港之上,是東北方的交匯處,也是首屈一指的運輸港口。城市的一邊是淚花之海,另一邊是港口。有人說只要掌控艾希佛斯,便控制了艾斯卡隆富裕的一方。艾希佛斯是離亞爾戈斯最近的堡壘,鄧肯深知道要是他想發動革命,那必然是他的第一站,他必須解放那曾經宏偉的城市。艾希佛斯的港口曾經泊滿揚著艾斯卡隆旗幟的船隻,現在卻換上了潘德夏的船,往日的光輝已成回憶。
鄧肯和艾希佛斯的統帥施維克曾經很親密。他們一起征戰沙場,合作無間,而鄧肯也曾多次與他出海。但自從侵略以來,他們便失去聯絡。施維克曾經是自豪的統帥,現在卻淪為卑微的士兵;既無法出海,也不能統治城市或到訪其他要塞,和其他統帥同一下場。他們也許已把他拘留,給他冠上「罪犯」之名,像所有艾斯卡隆的統帥一樣。
鄧肯徹夜趕路,他的人馬拿著火炬照亮了山丘,形成數百個向南移的火光。他們趕路的同時,雪越下越大,風越吹越烈。火炬或明或滅,月光被厚雲遮蓋。然而鄧肯的軍隊繼續推進,一日千里,這些士兵願意為他踏遍天涯海角。鄧肯知道夜間突擊是違反常理的做法,更不用說現在正下著雪了-但鄧肯一向不按常理行事,所以才能不停晉升,成為前國王的指揮官,擁有屬於自己的堡壘。就是這種革新的做法才令他成為四散的統帥中最受敬重的人之一。別人都做的事,鄧肯從不幹。他有一句座右銘︰做其他人意想不到的事。
潘德夏人鐵定想不到有人襲擊,因為鄧肯革命的消息還沒傳到南方來-只要鄧肯趕得上的話。潘德夏人絕對料不到他們竟會在夜間進攻,更別說是在風雪中攻擊了。他們知道在夜裏趕路相當凶險,也許馬匹會斷腿,還有無數其他問題。鄧肯知道,要打勝仗,必須出其不意;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速度。
鄧肯打算連夜趕路,直奔艾希佛斯,嘗試戰勝潘德夏的駐兵,以數百人之力把這偉大城市取回來。而假如他們能收復艾希佛斯,那也許他便能乘勢開戰,把整個艾斯卡隆全部奪回來。
「下面!」安溫在雪中一指,說道。
鄧肯俯視山谷,雪霧中有幾個小村莊散布在鄉郊。鄧肯知道那些村莊曾經有英勇戰士對艾斯卡隆一片赤誠。現在每個村莊只有少量壯丁,但也能湊合湊合,壯大聲勢,增加士兵的人數。
鄧肯在風嘯馬嘶聲之中朗聲叫道︰
「吹響號角!」
他的弟兄們吹起一系列短促的號角聲,那是艾斯卡隆往日號召士兵的聲音。他心頭一暖,實在太多年沒有在艾斯卡隆聽到這號角聲了。他的同胞會認得這把聲音,立即便會明白一切。假如這些村莊裏有熱血男子,這號角聲必定震撼他們的內心。
號角聲響了又響,他們走近村莊時,火炬慢慢燃亮了。村民察覺到他們的到來,開始在街上聚集,手上的火炬在風雪中搖曳;男丁們趕忙穿衣,拿起兵器,不管多粗製的盔甲都穿上。他們舉頭看向山丘,見鄧肯和他的人馬來到,個個手舞足蹈,似乎充滿驚奇。鄧肯能想像軍隊浩浩蕩蕩的在深夜於大雪中策馬而至的場面有多盛大;他們舉起幾百個火炬下山,彷彿一團烈火與風雪搏鬥。
鄧肯和他的人馬進入第一個村莊後,停下來用火炬照亮那些吃驚的面孔。鄧肯看著同胞滿懷希望的神情,於是擺出戰士的威猛神態,準備激勵他們。
「艾斯卡隆的子民!」他呼喊道。人們漸漸圍著他,他騎著馬轉來轉去,希望所有人都聽到。
「我們受潘德夏的壓迫太久了!你們可以選擇留在這條村莊如常過活,懷緬以往艾斯卡隆的美好日子;你們也可以選擇以自由人的身份起義,協助我們為自由而戰!」
村民不約而同衝前,大聲歡呼。
「那些潘德夏人擄走了我們的女孩子!」一個男人叫道。「假如這只是自由之戰,那我搞不懂解放的真義了!」
村民們歡呼。
「我們支持你,鄧肯!」另一人叫道。「我們願意和你共赴戰場,萬死不辭!」
村民又一聲歡呼後,匆忙的騎上馬,加入鄧肯的軍隊。鄧肯看到人數增加,甚感滿意,於是策馬離開村莊,這才發現艾斯卡隆等這場起義等得太久了。
他們很快到達另一個村莊,那裏的村民早就點起火炬,出來等候了。他們聽到號角和叫喊聲,看到軍隊人數大增,立即明白情況。當地的村民叫著彼此的名字,認出大家的樣子,一切心照不宣。這個村莊像上一個那般,二話不說為鄧肯傾巢而出。他們太渴望自由,誓要奪回尊嚴,於是全都拿起兵器上馬,加入鄧肯的陣營,誓死追隨。
鄧肯衝過一個又一個村莊,覆蓋整片鄉郊;所有村莊都在黑夜之中冒著風雪點亮火炬。鄧肯發現,他們渴求自由的心太強烈,甚至願意在最黑暗的夜裏發光發亮,拿起兵器,為重奪人生而奮戰。
*
鄧肯徹夜前行,帶領他的軍隊向南行,握著韁繩的雙手早因寒冷變得又紅又麻。他們開始接近南邊,地帶面貌也開始改變。佛理斯的乾冷天氣不再,換上的是艾希佛斯的濕寒天氣。空氣沉重,而且混和著海洋的濕氣和咸味,正如鄧肯記憶中一樣。這裏的樹木也比較矮小,而且被從不間斷的東邊猛風吹得歪在一邊。
他們翻過一座座山丘。雖然正下著雪,但月亮破雲而出,高掛在夜空為他們照亮前方的道路,讓戰士們在黑夜中趕路。鄧肯知道要是自己能存活下來,肯定這輩子都會記得這個晚上,因為這場戰役將會左右一切。他想到凱娜、他的家人和家鄉,他不願意失去這一切。他自己命懸一線,連他所愛的所有人都九死一生。今晚他便要孤注一擲,賭上一切。
鄧肯回首一看,很高興陣中多了幾百人,萬眾一心的進發。但他知道,即使人數增多,仍然是敵眾我寡。幾千名潘德夏人在艾希佛斯駐守,而且都是訓練有素的士兵。鄧肯知道施維克手上尚有幾百名解散了的將士可作調動,但當然沒有人能保證他會為鄧肯押上一切。鄧肯必須假設他不會這樣做。
他們很快又越過一個山丘,這次他們全都停下來,已經不需要再趕路了。那山丘下面的遠處就是淚花之海,海浪拍擊岸邊。宏偉的海港和艾希佛斯古城就佇立在淚花之海之上。城市似乎建於海中,海浪拍打著其石牆。城市背向土地,面向大海,城門和吊門沉在水中,似乎船隻比馬匹重要。
鄧肯細看著泊滿無數船隻的海港,懊惱的發現所有船隻都掛上潘德夏的旗幟。但見黃藍色的旗幟飄揚,他心下有氣。潘德夏的國旗迎風拍揚-一頭巨鷹咬著一個骷髏頭骨-鄧肯感到噁心。眼見如此偉大的城市被潘德夏控制,鄧肯深感羞愧,即使在黑夜中也能看到他面紅耳赤。船隻整齊的坐在海上,用錨穩妥的固定在一起,毫無防範。當然了,誰敢攻擊他們?何況是在風雪飄搖的深夜之中?
鄧肯感到所有人的眼光都放在他身上,他知道關鍵時刻已經來臨。大家都等待他一聲令下,而這個命令將會改變艾斯卡隆的命運。風颯颯而過,他坐在馬上,打從心底感覺到這是他的命運。他知道這是建功立業的時刻,也是這裏所有人揚名立萬的機會。
「進攻!」他大喝一聲。
他的人馬大聲喝彩,全都衝下山坡,向幾百尺外的港口湧去。他們高舉火炬,鄧肯心臟躍動,寒風拂過他的臉龐。他知道這次任務等同自殺,但正因這個主意太瘋狂,才有出奇制勝的機會。
他們一湧而下,彷彿撕破大地,馬匹疾風似的奔馳,迎面的寒氣急促得令鄧肯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們很接近港口了,距離石牆不過一百碼,鄧肯準備開戰。
「弓箭手準備!」他叫道。
他的弓箭手騎著馬,整齊的排在他後面;他們點燃了箭頭,等待他的指令。軍隊一直往前,馬蹄聲如雷,但坡下的潘德夏人還未察覺。
鄧肯等到他們靠近了一些-四十碼、三十碼,只餘下二十碼-終於他認為是時候動手了。
「放箭!」
黑漆漆的晚上突然被數千枝火焰箭照亮,劃破長空,穿過白雪,落在固定在港口的幾十艘潘德夏船上。火焰箭一枝接一枝像螢火蟲似的擊中目標,落在拍動不已的潘德夏船帆上。
船隻迅速著火,船帆和船身都燒起來了,火勢在風大的港口蔓延得很快。
「再放!」鄧肯喊道。
弓箭一波接一波,此起彼落;燃點了的箭頭像雨點一樣落在潘德夏的船隊上。
船隊在夜闌之中沒有動靜,士兵們都熟睡了,沒有人起疑心。鄧肯發現潘德夏人變得過份自負,安於逸樂,不可能預料到自己會受襲。
鄧肯不讓他們有集結的機會;他膽子大了起來,策馬向前,奔向海港,直達連接海港的石牆。
「火炬!」他喊道。
他的人馬立即衝到海岸線,高舉火炬,大喝一聲,隨鄧肯把火炬猛擲向離他們最近的船隻。沉重的火炬像木棍般砸在甲板上,砰砰作響,瞬間再多幾十艘船隻著火。
幾個當值的潘德夏士兵發現的時候已然太遲,身體也跟著起火,尖叫著跳入水中。
鄧肯知道很快所有潘德夏人都會醒過來。
「吹號角!」他叫道。
號角聲在士兵們之間不絕於耳,是艾斯卡隆以往的召集聲。他知道施維克會認出這短促的號角聲,心裏希望這樣能喚醒他。
鄧肯下馬,抽出佩劍,衝向海港圍牆。他帶領著軍隊,毫不猶疑的跳過矮小的石牆,跳上烈火洪洪的船上。他必須在潘德夏人聚集之前解決他們。
安溫和艾瑟菲爾和他一起向前衝,他的軍隊也加入,所有人發出震撼的戰爭吶喊聲,視死如歸。他們屈服了這麼多年後,報仇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潘德夏人最終給驚醒了。士兵們開始從甲板湧出,像螞蟻一樣一個接一個走出來,每個人都被濃煙嗆倒,一臉震驚,困惑不已。他們發現鄧肯和他的人馬,紛紛拔劍衝前。鄧肯面前不斷有士兵來襲-但他沒有退縮,相反更主動出擊。
鄧肯衝前,第一個敵人向他的頭顱猛砍過去,他頭一低避開,然後一劍刺入那人的內臟。另一個士兵劈向他背部,鄧肯轉身擋下-然後迅速格開他的劍,一劍插進他的胸口。
鄧肯四面受敵,但仍然英勇作戰,勾起了往時回憶。他深入敵陣,忙於擋開攻擊。敵人距離太近,他無法揮劍,只得往後一仰,把他們踢開,為自己製造揮劍的空間。有需要的時候,便轉身用手肘攻擊,赤手空拳近距離打鬥。圍著他的敵人全都倒下了,沒有人能傷他半分。
鄧肯很快看到安溫和艾瑟菲爾聯同幾十人衝前來幫忙。安溫上前擋下了瞄準鄧肯背心的弓箭,免他受傷-而艾瑟菲爾則踏前,為鄧肯舉劍擋下斧頭攻擊;鄧肯隨即上前把那士兵刺死。他和艾瑟菲爾兩人合力了結他。
他們同心戰鬥,多年來合作使他們像一部運作暢通無阻的殺人機器,在刀光劍影的晚上守護著彼此。
鄧肯四周的人馬正在海港的船上來來回回發動攻擊。一連串潘德夏士兵向前進,所有人都完全醒過來了,有些人身上著火。艾斯卡隆的戰士在烈火中勇敢戰鬥,即使陷入火海仍然不肯退縮。鄧肯戰鬥至再也無法舉高雙臂,全身濕透,煙燻雙眼。佩劍啷噹的聲音響起,敵方士兵一個接一個想要逃到岸邊。
終於,火勢太猛烈了;潘德夏士兵全副武裝卻被困在火海之中,於是跳船求生-而鄧肯帶領他的軍隊離開船隻,躍過石牆,回到海港邊。鄧肯聽到一聲叫喊,他回頭看到幾百個潘德夏士兵正要跟上他們,從後追殺。
他跳到岸上,等到他最後一個弟兄也上岸了,才回過身來,舉高佩劍,一劍砍開那些把船隻繫在岸邊的繩索。
「斬斷繩索!」鄧肯叫道。
他的軍隊跟著他站在海港來來去去,把繩索斬斷。鄧肯眼前的繩索終於斷開,他一腳踏在甲板上,用力一蹬,把船隻推離岸邊。他花了不少力氣,不禁呻吟了一聲。安溫、艾瑟菲爾和幾十人衝前照做。他們合力把燒得正旺的船隊推離岸邊。
那些烈焰騰空的船上充斥著士兵的慘叫聲,無可避免的漂向海港中的其他船隻-一碰上後,另一艘船便也燒了起來。幾百人跳出船隻,尖叫著沒入漆黑的水中。
鄧肯站在那裏,呼吸急促,默不作聲的看著;他雙眼發光,整個海港瞬間變成一片火海。幾千名潘德夏人全都醒來了,從其他船的低層甲板走出來-但一切都太遲了。他們眼前是一面火牆,要不是活生生被燒死,就是跳入冰冷的水中淹死;他們全都選擇了後者。鄧肯看著幾百人迅速填滿海港,在水面上漂浮著,一邊叫喊著,一邊游到海岸。
「弓箭手!」鄧肯立即叫道。
他的弓箭手瞄準後,箭接箭的發射,目標是那些亂動亂叫的士兵。他們箭法神準,潘德夏人沉沒於水中。
水面染成一片血色,很快傳來噬咬的聲音,當中伴著士兵們的尖叫聲。水裏住滿了發光的黃鯊,在血腥的海港飽吃一頓。
鄧肯眺望這一切,慢慢才意識到自己幹了甚麼事情︰整支潘德夏船隊在幾個小時前那麼明目張膽的停泊在海港,象徵著潘德夏的佔領,在頃刻間已無影無蹤。幾百艘船給破壞掉,燒得乾乾淨淨,鄧肯大獲全勝。他講求速度和出其不意的戰術湊效了。
他的軍隊中傳來一聲呼喊,鄧肯回頭見他們看著船隻給燒毀而歡呼,臉上盡是黑黑的煤灰。徹夜趕路令他們筋疲力盡,但他們全都陶醉在勝利之中。那是解脫的呼喊,等了多少年才終於叫了出來。
然而他們歡呼聲未落下,便傳來另一種叫聲-帶有威嚇的味道-緊接著的聲音令鄧肯毛骨悚然。他回頭一看,心頭一沉,那大石軍營的大門正慢慢打開,露出了駭人的景象︰幾千名潘德夏士兵全副武裝,排列整齊;那是訓練有素的軍隊,人數是鄧肯那方的十倍,正準備應戰。大門打開後,敵方大喝一聲,向他們衝過去。
猛獸已然驚醒。真正的戰爭現在才要開始。
第六章
凱娜緊握著安鐸的馬鬃,在黑夜中馳騁。蒂德蕾在她身邊,李奧在她腳邊,像小偷要連夜逃亡似的向亞爾戈斯城西邊白茫茫的平原奔馳。她直騎了好幾個小時,馬蹄聲在她耳中砰砰作響。凱娜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想像厄爾之塔有甚麼事情等著她、她的舅舅是甚麼人。想到他也許會說出她的身世,還有她母親的事情,她便無法抑壓內心的興奮。但她也必須承認心中的恐懼,畢竟這是她頭一回如此橫跨艾斯卡隆國境,路途相當遙遠。而她看見陰森森的荊棘之林已立於他們眼前,開揚的平原已經來到盡頭。他們很快便會深入幽森恐怖的森林,裏面猛獸滿布。她知道一旦踏入森林,所有常規都不管用了。
寒風凜凜列列的吹過平原,白雪拂打著她的臉。凱娜雙手早已麻木,火炬脫手時才發現原來早就熄滅了。她在黑暗中策騎而行,陷入沉思之中,只聽得馬蹄踏踏,腳下雪沙沙作響,還有安鐸偶然發出低聲吼叫。她感覺到他的憤怒,果然天性難馴,與她騎過的任何野獸都不一樣。安鐸似乎不但對前路毫不畏懼,反而渴望戰鬥。
凱娜披著毛皮大衣,肚裏又一陣飢腸轆轆。她聽到李奧再次哀鳴,知道他們再也不能對自己的肚皮置之不理。他們騎行幾個小時,早已吃光冷凍肉條;她這才知道帶的糧食不足。下雪的晚上沒有甚麼小獵物,只怕不是好兆頭。他們必須停下來找食物。
他們慢慢接近森林的邊緣,李奧對著黑漆漆的林木叫吠。凱娜回頭看著通向亞爾戈斯城的那大片平原,抬頭瞧了遼闊的天空一眼,恐怕有一段時間都看不到了。她回過頭來盯著森林,內心有點不願意前進。她深知荊棘之林臭名昭彰,而她也明白,一旦踏出這一步,便再也不能回頭了。
「你準備好了嗎?」她問蒂德蕾。
蒂德蕾現在看來和當時逃離牢房的女孩判若兩人。她變得更堅強、更堅定,彷彿已從地獄活著回來,再也天不怕地不怕。
「更糟的事情我也經歷過。」蒂德蕾說道,聲音像眼前的樹木一樣冷冷冰冰,以她的年紀來說太蒼老了一點。
凱娜會意的點了點頭-她們並肩出發,走進樹林。
他們一踏進森林,凱娜立即感到一股寒意,卻與寒夜的感覺迥異。森林更黑暗、更幽閉,到處都是古老的黑色樹木,扭曲的樹枝形若荊棘,樹葉又厚又黑。這片森林散發的不是平和的氣息,而是邪氣。
他們開始加快腳步,在樹林間盡快前進。冰雪在她們坐騎下嘎嘎作響,樹枝之間漸漸傳來奇怪生物的聲音。她轉頭掃視著樹枝尋找聲源,但一無所獲。她覺得他們已被盯上。
他們深入樹林,凱娜按照父親的指示,盡量向西北方走,直到看到大海為止。他們一邊走著,李奧和安鐸向隱於林中的生物低吼,但凱娜甚麼都沒看到,只是低頭躲開樹枝,避免刮傷。凱娜琢磨著面前的漫漫長路,她雖對自己的任務感到興奮,卻也渴望與她的人民在一起,在她發動的戰爭中並肩作戰。她早已心急如焚,想盡快回去。
幾個小時後,凱娜凝視著樹林,納悶著還要走多久才看到大海。她知道在黑夜中騎行很危險-但在這種地方野營更可怕-況且她又聽到嚇人的聲音了。
「大海在哪裏呢?」凱娜終於開口問蒂德蕾,一心只想打破沉默。
她從蒂德蕾的表情知道自己打斷了她的思緒;天知道她陷入何等惡夢之中。
蒂德蕾搖搖頭。
「我也想知道。」她答道,聲音乾乾的。
凱娜一臉困惑。
「他們帶你走的時候,不是走這條路嗎?」她問道。
蒂德蕾聳聳肩。
「我被關在馬車後面的籠中,」她答道。「幾乎全程失去知覺,他們走哪個方向我都不知道,我不熟悉這片森林。」
她嘆了一口氣,凝視著黑夜。
「只要我們走近白木森林,我應該能認得更多路。」
她們繼續上路,慢慢沉默下來,凱娜不禁對蒂德蕾的過去感興趣。她強悍,同時充滿悲傷。凱娜開始被黑暗思緒侵蝕,前路茫茫,既沒有食物,而且寒風刺骨,還有猛獸虎視眈眈。她轉向蒂德蕾,希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告訴我厄爾之塔的事吧。」凱娜說。「那裏是怎樣的?」
蒂德蕾回頭看著她,眼窩下還帶著一圈瘀青。她聳聳肩。
「我從沒去過那座塔。」蒂德蕾答道。「我來自厄爾,要向南騎行一整天才到達厄爾之塔。」
「那跟我說說你的城市吧。」凱娜說道,不願想著這片森林。
蒂德蕾雙眼亮了起來。
「厄爾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她帶著憧景說道。「是海邊城市。」
「我們城市的南方也有一個近海的城市,」凱娜說。「叫艾希佛斯,離佛理斯只有一天的路程。小時候我常常跟父親到那裏去。」
蒂德蕾搖搖頭。
「那不是海。」她答道。
凱娜困惑起來。
「甚麼意思?」
「那是淚花之海。」蒂德蕾答道。「厄爾在悲愴之海,比淚花之海廣闊多了。你們東岸只有一些小海浪;在西岸,潮漲的時候海浪高達二十尺,連船隻都能在一瞬間捲走,人更不消說了。我們城市的懸崖不高,容許船隻靠著陸地停泊,在艾斯卡隆獨一無二。而且我們的城市擁有艾斯卡隆唯一一個沙灘,所以首都安德羅斯才會建在我們東邊,不過一日路程。」
Конец ознакомительного фрагмента.
О проекте
О подписке